陈夏把最后一台空调外机的包装拆开时,额头上的汗已经顺着下颌线滴进工装领口。六月的随州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,他蹲在小区绿化带旁拧开矿泉水瓶,喉结滚动的声响在蝉鸣声里格外清晰。
“小陈师傅,歇会儿不?” 三楼的张阿姨探出头,手里端着个青花碗,“刚做的葛粉凉粉,来尝尝?”
瓷碗边缘凝着细密的水珠,透明的凉粉里卧着几粒饱满的葡萄干,红糖浆在碗底漾出琥珀色的涟漪。陈夏犹豫着接过,指尖触到碗壁的凉意时,忽然想起十年前的冬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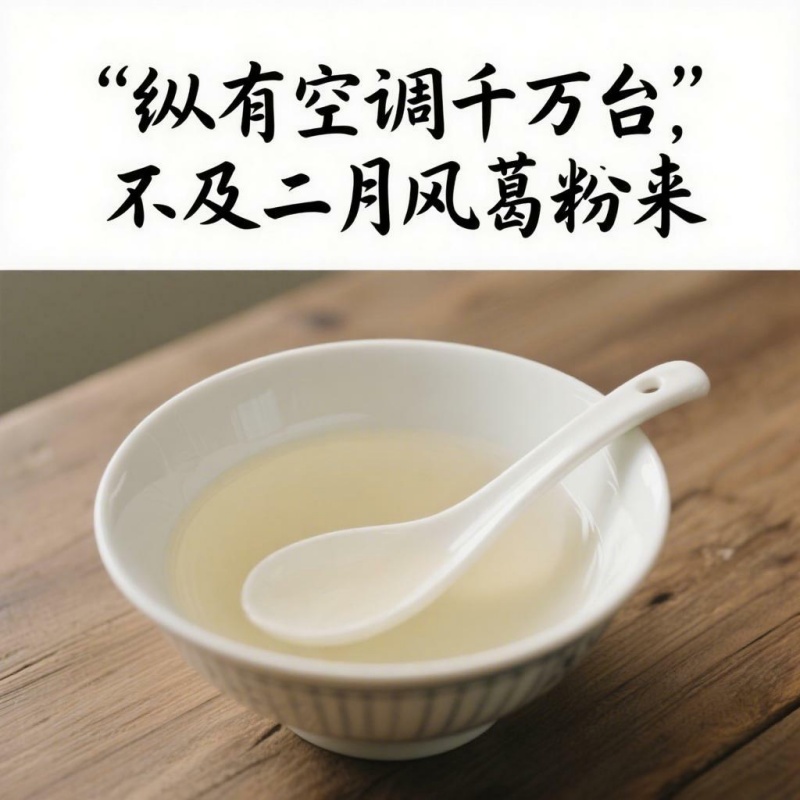
那时候他还是个半大孩子,跟着爷爷住在大洪山北麓的老屋里。山里的冬天冷得透彻,但霜降过后,采葛根的时节就到了。爷爷总爱在清晨的薄雾里,背着竹篓带着他上山。“霜降后的葛根才够味,经了霜打,淀粉沉淀得足。” 爷爷踩着厚厚的落叶往前走,拐杖敲在冻硬的土块上,发出笃笃的声响。
爷爷认得哪片坡上的葛根最粗壮,他用特制的小镢头小心刨开冻得紧实的泥土,葛根表皮的绒毛沾着冰碴,像块刚从雪地里翻出来的璞玉。“这东西金贵着呢,得三年以上的才够劲儿。” 爷爷边说边把断裂处渗出的乳白汁液抹在他冻得通红的鼻尖上,凉丝丝的舒服。
回家后,爷爷会把葛根倒进院里的青石缸,用带着冰碴的山泉水泡上半天。然后坐在小马扎上,拿着铜刨子细细地擦,乳白的葛浆混着碎渣沉在水底,像揉碎了的月光。接下来是最费功夫的过滤,用细纱布裹着葛渣反复挤压,直到滤出的汁水清得能看见缸底的青苔。
爷爷坐在竹凳上翻搅着沉淀的葛粉,阳光透过屋檐的缝隙落在他手背的老茧上,“这手艺啊,得慢慢磨才出好东西。” 那时候陈夏不懂什么叫门道,只记得爷爷把沉淀好的葛粉倒进竹匾,冬日的阳光晒在粉面上,扬起细小的金尘。攒下的葛粉装在陶瓮里,能吃一整个夏天。
张阿姨的凉粉滑进喉咙时,陈夏忽然懂了那种熟悉的清凉。不是空调风直愣愣的冷,是像山涧水漫过脚背的温润。他抬头看见阳台晾着的标签 —— 随州市二月风食品有限公司,旁边印着行小字:源自清同治元年赵家葛坊。

“这葛粉真不错,比超市买的细腻多了。” 陈夏把空碗递上去,“阿姨在哪买的?”
“就在街口那家特产店,说是用的大洪山霜降后的野生葛根,还保留着老手艺呢。” 张阿姨指着包装上的图案,“你看这采葛的法子,跟老辈人说的一模一样。”
傍晚收工时,陈夏特意绕到那家店。玻璃柜台里整齐地摆放着二月风有机野生葛粉,他仔细看了看,选了两袋。结账时老板娘笑着说:“很多年轻人都爱用这个做果冻,放些芒果丁,孩子抢着吃。”
回到出租屋,陈夏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调葛粉糊。沸水冲下去的瞬间,透明的浆液泛着微光,像极了爷爷当年在青石缸里沉淀出的模样。他没放红糖,只撒了把从老家带来的野蜂蜜。
晚风从纱窗溜进来时,瓷碗里的凉粉还冒着丝丝凉气。陈夏咬下一口,忽然听见遥远的蝉鸣里,混着爷爷刨葛根的叮当声。原来有些味道从来没变过,就像这藏在葛粉里的夏日风,穿过十年光阴,依然能吹得人心里清亮。
他掏出手机给爷爷打视频,老人正在院坝里翻晒新收的玉米。“爷,我今天吃凉粉了,跟你做的一个味儿。” 陈夏举着碗对着镜头,“今年霜降后,咱再进山采葛根吧?”

屏幕那头的爷爷笑得露出牙床,蒲扇摇得更欢了:“好啊,等你回来,咱用新收的野生葛粉做果冻,给你小侄女尝尝。”
窗外的霓虹灯次第亮起,陈夏把最后一口凉粉咽下去。这个夏天,好像突然有了些不一样的盼头。

